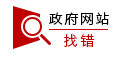导读
长期以来,广播电视作为覆盖面最大、受众最多、最具影响力的传统大众媒体,对国家、社会、公众生活的方方面面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以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为载体的新兴媒体综合运用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形式,将原来由报纸、电视等媒体承担的功能融为一体,媒体传播方式、传播内容的界限日渐模糊,媒体传播的移动化、视频化趋势愈发凸显,媒体融合不断深入,视听媒体传播空间和影响力持续拓展。媒体融合发展,对广电立法提出了新要求。 2020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强调,要积极推进重要领域立法,健全国家治理急需的法律制度、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必备的法律制度,以良法善治保障新业态新模式健康发展。新时代如何将包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等大量视听新媒体纳入法治轨道,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和法治中国建设的基本要求,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做好广播电视行业的管理和服务,首先应当加快推进《广播电视法》立法工作,并在立法时注意处理好以下三大关系。 一 处理好严守内容安全底线和促进视听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关系 广播电视是党和政府重要的思想宣传阵地,通过正确的舆论导向,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工作任务、工作方法传达、落实到全社会,巩固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地位,是广播电视工作的“根”与“魂”。制定《广播电视法》,必须旗帜鲜明地贯彻落实党对广播电视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注重法治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作用,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要求体现到《广播电视法》的具体制度条文中;同时,强化政治安全、内容安全的底线意识,加强制度设计,营造风清气正的视听媒体传播空间。 在牢牢把握正确导向、严守内容安全底线的前提下,如何让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深入人心,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一方面需要不断创新宣传方式,丰富宣传手段,提升宣传的实效性;更需要的是在法治的轨道上不断支持和促进广播电视以及整个视听媒体行业的繁荣发展,使其更好地承担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这就要求《广播电视法》的制定应当改变过去行业立法“重管理限制、轻保障促进”的立法理念,强化对广电市场主体经营自主权、知识产权等权利的保障;注重财税、金融等措施在广播电视行业发展中的促进作用,完善广播电视人才培养体制机制。 同时,法律宜按照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逐步提升市场机制在广播电视资源配置和利益分配中的重要地位,引入利益引导机制,对于积极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制作、传播主体,给予物质扶持和精神奖励;优化行政审批,鼓励多元化广播电视消费模式,提升广播电视机构营收能力和市场活力,推动推出更多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的正能量广播电视作品;完善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赋予网络视听等视听新媒体在推进视听媒体服务均等化、可及性方面的公共义务,在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广播电视文化需求的同时,不断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 二 处理好视听媒体统一规范和差异化管理的关系 从技术发展角度来看,广播电视是伴随着无线电信号的发现和频率资源的利用,逐步步入人类社会舞台。从最早出现的无线广播开始,经过无线电视、卫星电视、有线电视,再到互联网电视、IPTV,广播电视作为对图像、声音进行传输的大众传播手段,受众的公共性,节目根据事先编排的节目单按顺序播出,用户对节目不具有选择权,一直是其最主要的特征。 然而,随着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等技术的快速发展,图像、声音等视听信息在互联网平台上以一种更为个性化的方式进行传播,用户可以在互联网视听服务商提供的点播目录中自行选择观看时间、观看内容,不受既定的节目编排表的限制。同时,互联网作为信息传播载体,允许用户上传大量原创制作的视听内容,视听节目内容和形态极大丰富,更大程度上推动了网络音视频、网络直播等业态的迅速发展。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12月,我国网络视频(含短视频)用户规模达9.27亿,占网民整体的93.7%;网络直播用户规模达6.17亿,占网民整体的62.4%;网络音乐用户规模达6.58亿,占网民整体的66.6%。传统以广播电视为主要传播方式的视听媒体已逐步向互联网、移动互联网迁移,网络视听成为可以与广播电视分庭抗礼的重要产业构成。特别在媒体融合背景下, 4K/8K、5G、云计算、人工智能、大数据、虚拟现实、区块链等新技术的融合应用将进一步对传统的广播电视行业带来更大的冲击。 随着2018年党和国家机构改革落地,新组建的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对广播电视以及网络视听等视听媒体的管理职能进一步聚焦。这就要求《广播电视法》的调整范围需要在传统的广播电视行业之外,逐步向网络视听等视听媒体新业态、新模式进行扩展,并体现出立法包容性和前瞻性。在导向监管上,坚持对所有视听媒体实行一个标准,构建网上网下同心圆。同时,由于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等视听新媒体,在传播方式、商业模式以及经营主体性质、经营方式、经营规律、国家财政支持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别,在具体制度设计中,需要坚持分类管理原则,针对不同的业态匹配差异化的管理措施。如传统的广播电视是按照既定节目表及时间顺序向公众播出视听节目,属于一对多、点对面的大众传播,广播电视播出机构应当对节目表进行审核及调控,避免错播、空播,不得擅自插播;而网络视听则属于用户自行点播的视听媒体服务,网络视听服务提供者需要对视听媒体库中的所有内容进行审核,避免出现法律禁止的内容,并针对用户参与互动、发表评论的行为,承担相应的内容审核义务。 三 处理好广播电视法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衔接配合关系 按照我国的立法体制,《广播电视法》属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效力层级仅次于宪法的基本法律。作为行业发展的“母法”,《广播电视法》首先要处理好与广播电视行业现行有效的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如《广播电视管理条例》《有线电视管理暂行办法》《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管理规定》《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专网及定向传播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等的关系:将实践证明正确而又行之有效的好的制度上升到法律层面;对于目前还看不准但又迫切需要立法的,可以先把原则确定下来,为行业今后的发展留出空间;对于实践证明已经不适应新形势发展要求,将成为行业发展障碍的内容,进行修改或废止,形成内部协调统一的广播电视法律制度体系。 其次,《广播电视法》还需处理好与相关法律,特别是《著作权法》《网络安全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广告法》以及电信、文化领域相关立法的衔接配合问题。例如新修订的《著作权法》第十条第(十一)项规定,著作权人享有广播权,即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公开传播或者转播作品,以及通过扩音器或者其他传送符号、声音、图像的类似工具向公众传播广播的作品的权利,但不包括本款第十二项规定的权利(即信息网络传播权)。在《著作权法》对该权利形态未作具体细化的情况下,《广播电视法》是否需要对此予以明确,如何保证相关制度间的协调。《网络安全法》关于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网络信息安全制度、实名制等制度要求如何在广播电视领域特别是网络视听领域落地;《未成年人保护法》关于保障未成年人免受危害其身心健康广播电视节目影响等规定,如何在《广播电视法》中进行有效回应等,均需要在立法过程中得到妥善解决。 立法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加快推进《广播电视法》立法工作,是在当前数字技术日新月异,媒体深度融合大背景下的必然选择。随着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的深入推进,要妥善处理好立法过程中需要权衡的各种关系,制定出一部符合时代要求、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广播电视领域基本法律。 (供稿单位:腾讯研究院 执笔人:汤捷)

 登录
登录